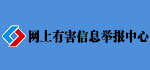在两宋,民间势力或与国家合作兴办水利,或独资兴建水利,这其中既有自身利益的驱使,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激励,亦有提高自身地位以及社会威望的需求,多种动机夹杂在一起,促使他们投身于地方水利事业,他们在水利兴建工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宋代民间势力参与兴建水利的事例极为繁多,遂,所选史料不仅限于浙西路,亦涉及其他地区,旨在说明,民间势力参与兴建水利工程,并不仅仅是浙西路独有的现象,放眼两宋其他地区,也大多如此,而浙西路不过是宋代水利社会的一个缩影罢了。
一、民间势力与国家联合兴建水利
两宋水利事业的兴办,出现了国家与民间合作或民间独资修建水利的方式,这极大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。
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极大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,一般而言,只有国家有能力主持兴建,民间势力并不具备这样的势力,因而,在大中型治水活动中,国家占主导地位,不过,并不排斥民间力量的参与,遂会出现民间势力和国家联合修建水利的情况。
在浙西路,民间势力与国家联合兴建水利的例子屡见不鲜。在开浚华亭等处沿海三十六浦的过程中,国家负责措置钱谷,民间负责出力,国家与通力合作,共同兴建水利。
昆山县四浦疏浚工程,由国家负责支出钱米,并派官员监督,民间受利人户则负责出力,官民合作,共修水利。绍兴二十八年八月二日,赵子潚上奏说:“子潚等契勘,昆山县四浦工力不多,乞止用本县食利人户,支给钱米,委本县官监督开浚。”
秀洲的置闸工程,由国家倡办,民间则负责出钱出力。乾道二年,知秀洲孙大雅言:“州有柘湖、淀山湖、当湖、陈湖,支港相贯,若于诸港浦置闸启闭,不惟可以泄水,而旱亦获利。然工力稍大,欲率大姓出钱,下户出力,于农隙修治之。”民间百姓,凡水利受益者,无论上户还是下户,都会在水利兴建过程中有所付出。
还有一种合作方式是,国家委托民间管理水利。在这种方式下,官府是水利工程建设的出资方,水利工程修建完成后,亦常遇到河道淤塞等问题,而国家没有办法时常关注,遂会借助当地有威望,有实力的民间势力负责后续维修工作。可见,对于堤岸、陂塘等小型的水利工程的日常管理工作,会由近水受益之家负责,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国家对民间的骚扰,还能提高效率。
除了浙西路外,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很多官民联合兴建水利的现象。余姚县海堤的兴建是由国家与民间共同合作完成,其中,县政府负担了一小部分资金,即四千二百余钱,县之士夫和乡人等民间势力则承担了一大部分资金,即三百万。
象山县的朝宗石,亦是由官民联合修建完成。朝宗石创建于元祐元年,绍兴年间,宋砥任象山县令,计划重新修整,无奈公私窘匮,财政匮乏,所以,宋砥号召耆老,希望他们能出资援助,完成此次工程的兴建。
经过探讨,决定先由耆老们筹资,其后,由官府负责组织,通过贩卖灰壤、竹头、木屑等特产的方式,赚钱兴修水利,“岁时之久,得钱三百万有奇。不费于公,不取于民,而仅以足用。”
在当地官府和耆老们的共同努力下,最终完成了此项工程。隆兴年间,赵彦逾任象山县令,当地人请求重修朝宗石,于是,官府承担了一部分兴修水利的费用,民间势力负担了剩余部分的经费,其中,民间部分“粒一十四斛有奇,稻一十一斛有奇,皆庵僧募于好施者。”
泗州护城堤也是在官民的联合努力下才修建完成的。景祐年间,泗州泗守张侯治淮,准备修筑护城堤,因原来的堤岸破旧所以打算扩建,“度为万有九千二百尺,用人之力八万五千。”
泗州人民听说后说,“此吾利也,而大役焉。然人力出于州兵,而石出乎南山,作大役而民不知,是为政者之私我也。不出一力而享大利,不可。”于是,民间“相与出米一千三百石,以食役者。”堤成,高三十余尺,堤坚石固,抗暴备灾,民享其利。
二、民间力量参与水利事业的动因
有很多民间力量参与水利兴建活动,然而,又有何种原因,促使他们奉献如此之多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,积极投身于水利事业的建设当中呢?民间力量参与水利事业的动因是多方面的,具体分析如下。
1.自身利益需求
自身利益的需求是民间势力参与水利建设的动机之一,他们出钱、出力,亦有人捐余俸,尽己所能投身于水利事业,对社会做出了极大贡献。如范武,“邑士范武倡为义役,捐以助修筑。”如李宏,更是为修建木兰陂付出自己的全部家财与生命。如“食利之民”,也参与水利活动,其中富裕的上户和中户出钱出米,较为贫穷的下户出力,共同兴建水利。可想而知,民间势力为兴修水利,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与金钱。
首先,部分民间势力之所以参与兴建水利,是因为他们是水利工程修建完成后的直接受益者。其中,有很多民间力量是在国家的倡导下,加入到水利工程的修建当中。宋代,在水利工程的修建过程中,民夫征调以及资金筹集大多来自于受益人户,国家把水利工程受益人户的利益和责任联系起来,极大的调动了受益人户参与水利建设的积极性。
仁宗嘉祐年间,宜兴邑尉阮洪“深明宜兴水利。方是时,吴中水,洪屡上书监司,乞开通百渎。监司允其请,遂鸠工于食利之家,疏导四十九条,是年大熟。”在邑尉阮洪带领,食利人户参与了疏导宜兴四十九渎的水利工程,一句“食利之民”点出问题的关键所在。
仁宗年间,两浙提点刑狱使宋纯,谋划在本路兴建水利设施,他向国家建言,工程建设需要的“方下本属州军计夫料、饷粮,设法劝诱租利人户情愿出备”。这里的“租利人户”,指的是收租食利人户,即农田主,他们亦是水利工程完成后的实际受益者。
乾道六年十二月,监进奏院李结献治田三议:一为务本,二为协力,三为因时。其后,工部认为三议妥当可行,但工程浩大,遂令有田之家按田地数量出资修筑,“但工力浩瀚,欲晓有田之家,各依乡原亩步出钱米与租田之人,更相修筑,庶官无所费,民不告劳。”
此外,还有还有些水利受益人户,自觉参与兴建水利。一些较为富裕的民间力量,他们在当地占有较多的土地,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,因此,修建水利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,所以他们比其他人更关心水利事业。
如钱侃修筑东湖塘,有一部分原因是族人在湖边多有田产,此举可以直接造福子孙,使自己的族人和后代获得极大利益。如余彦诚,他兴修废堰,不但能灌溉邻里良田,关键是还能灌溉己田,“彦诚用家钱百万修废堰,潴源水,遇旱岁,无高下彼我均浸之,邻里沾足。”
余彦诚花百万家资兴修水利,可见,他为当地一富户,家境充裕,颇有家财,在当地当有众多田产,修建废堰,首要获利者即为他本人。还有参与修建木兰陂的十四家,他们皆为“食陂之利者”,是木兰陂建成后的直接受益人。
其次,参与兴建水利的民间势力,还能获得国家的额外奖励,这亦刺激一部分民间力量投身到水利工程的兴建当中。如与李宏一起参建木兰陂的十四家大姓,就因捐钱修陂而受到国家嘉奖。元丰四年,宋神宗将陂田四百九十亩七分赏赐给十四家,并免其粮差,永为圭田,昚乃世守。十四家因参建木兰陂工程,获得了四百余亩“不科田”,获利颇丰。
可见,在自身利益需求的刺激下,很多民间势力出钱、出力,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与金钱兴建水利。
2.强烈的社会责任感
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亦是民间势力参与水利建设的动机之一,他们投身于水利事业,为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首先,宋代士人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刺激下,积极参与水利建设。鉴于前代藩镇割据的局面,北宋建国初期,就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,对武人防备甚严,重文轻武。同时,两宋还极为重视科举制度,因而,民间非常重视教育,读书中举几乎成为每个个人和家族的奋斗目标。
两宋文臣通过科举制度中举作官,成为官僚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。因此,在科举的影响下,宋代士人大多是集学者、官僚、文士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,即士大夫,他们常常拥有极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不但胸怀天下,亦关怀乡土。
他们有些是隐居、退休或者丁忧而居住乡里的官员,有些是在朝为官心怀家乡的在职官员,有些是乡居士人,有些是未仕士人,这些士人多品德高尚,在当地有极高威望,如陈亢在当地颇具盛名,时人邹公浩赞扬他“仁义之声,飞驰东南”。如陈纬,“复捐廪以赈饥,给药以济病。人呼为陈义士。”
这些投身于地方水利事业的士人,对乡土有着真挚恳切的关怀,这种感情,超越了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,展现出济助世人的高尚情怀,他们是地方的楷模,为了乡里民众的全局利益,积极投身于地方水利事业,造福乡里。
如,婺州士人潘好古,他出资重修西湖旁的两个废塘,但“时公未尝有寸田居其间”,潘好古在废塘附近并无半寸土地,可想而知,他此次修塘并不是为谋个人私利,有人问他出资修建废塘的原因,他回答说,“乡邻安则吾安矣”。
可见,潘好古出资重修废塘,不是为谋私利,而是为了灌溉乡里良田,造福百姓。还有湖州士人刘定国,关心民众,见平辽、尚吴二渎和李氏埭,年久失修,家乡常遭水患,为百姓安居乐业,于是,他率乡人修筑水利。由此可见,以潘好古、刘定国等为代表的乡居士人,参与兴建水利事业,并不是为谋个人利益、沽名钓誉,而是关怀乡里,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有意造福于民,福泽乡里,实为地方表率。
其次,普通民众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刺激下,亦积极参与水利活动。这些民间势力,虽不是士人,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亦使他们投身于伟大的水利事业,如钱四娘,虽非士人,亦非莆田本地人,在莆田更无任何田产,可想而知,她四处募捐、倾尽家财修建木兰陂,并不是为个人私利,而是为了莆田民众的整体利益。她不忍莆田民众饱受水灾之苦,遂坚定不移地投身于莆田的水利事业。
提高社会地位及社会声望亦是民间势力参与水利建设的动机之一,他们兴建水利,造福乡里,为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宋代建国后,鉴于前代藩镇控制财政的现象,实施地方财政收归中央的策略。地方政府征收的酒税、商税等赋税,每年按一定比例上交中央,而地方只留固定的一小部分支撑正常运转。中央政府通过实施财政中央化政策,把持全国各地财富,出现资源独占的局面。
大量地方财富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央,造成地方财政压力过大,负担较重。在地方财政资金极为紧张的情况下,地方政府一般很难展开水利建设,这就为民间势力参与到水利活动提供了机会。
总结
民间势力就此机会参与水利事业,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威望。如参加木兰陂兴建的十四家大族,“子孙继是役者,年有酬劳,日有食钱,盖以先世有功于陂,故特加优厚,宏治间,邑人御史周进隆疏于朝,檄下,本府县春秋祭宏,十四人者皆得与享云。”
木兰陂建成后,十四家大姓的社会声望、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,并负责轮流巡视和修治木兰陂工程,变成了木兰陂的实际管理者和领导者,并且,这项权利还世代相传,十四家的子孙后代依然享受这个权利,甚至到元明清时期,十四家的子孙后代,在莆田依然有着较为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。
可见,民间势力通过组织、参与地方水利事业,有助于他们提高自身或家族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威望。